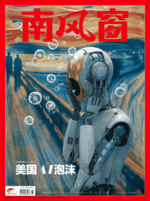2025年3月24日,浙江杭州,市民们在滨江樱花大道上骑行、散步(图/视觉中国)
“明天上午十点钟会有暴雨。”周霏强从口袋里把手机掏出,喃喃自语道。
3月初的杭州,全中国最炽热的目光都聚集于此。AI、机器人,来自赛博世界的风云和“六小龙”,搅动西湖一池春水。
但周霏强关心的是具体的天气。他是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副总经理。“雨来,骑车的人就会明显变少了。”
可是,AI都改变世界了,一辆自行车还重要吗?商业共享单车都进入成熟期了,一辆由政府主导、企业运作、公益属性的公共自行车,还重要吗?
厦门、无锡、武汉等许多城市,都已经放弃了公共自行车。杭州为什么还要做?
当杭州站在AI时代的风口,用六小龙造出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时,仍有人真切地关心每一场真实的风雨。
这是一项实实在在与人相关的公共事业,与机器人、大模型都不同。它不需要借助电波存在,关心的是最朴素的人民出行、休闲需求。它为赶路的人提供免费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也为畅游西湖的游客,献上本地化的无声陪伴。
2008年,杭州最早从欧洲城市“引进”落地了这项公共事业,为公众解决短距离出行需求。
当我们在追问,为何是杭州酝酿出科技六小龙时,回过头或许会发现,在骄傲的大时代里,杭州早已用一辆小红车,笼络住了普通人的一颗心。
骑
吴安家住湘湖边,小区门口列有一整排小红车。空闲时,他就会借一辆小红车,环着湘湖骑行。“从家里出发,跑一圈,正好回来还是还到那个点位,很方便。”
从2008年第一辆小红车投入使用到今天,17年的时间过去,似乎人们已经习惯街边停靠着一辆可以阶段性免费使用的红色单车。
西湖边的杨公堤,一辆从余杭区穿越而来的小红车,展示了杭州人民的“骑行力”—地图显示,从余杭区骑行到杨公堤,需要大约两个小时。
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总经理助理金根胜告诉南风窗,大部分市民的骑行需求集中在20分钟到30分钟之内,所以小红车首先可以免费使用1个小时。但通过“延时还”等叠加功能,最多是3小时免费,“三个小时有什么事情也都办好了”。
杭州人的骑行力,同样与城市规划的骑行友好理念密切相关。
绿野仙踪一般的杨公堤,非机动车道占了40%的道路宽度;在景区外道路的十字路口,非机动车道也拥有自己的右转辅道和红绿灯。柏油路平整,交叉口规则清晰,绿化带里种满各式各样的鲜花。2022年,杭州是唯一一个进入全球自行车指数前十的中国城市,排名第七。
背靠着完善的市政规划,在大部分城市无力支撑公共自行车运营的今天,“小红车”日租用量最高达到47.3万人次,免费使用率达到98%。
2012年,小红车用9处小红车点位的616吨碳排放量,从北京环境交易所换回了两万余元。这是一次公共自行车行业内绝无仅有的碳交易尝试。
一辆坚持绿色事业的小红车,也在坚持“与时俱进”。
不需要市民卡,不需要押金,部分车也不需要实体还车桩,还有临时停车和隔夜还车的选项。为了骑行的舒适度,其车胎换成了更减震的气胎,把速比调到了2.0比1,把脚踏板拉宽;为了安全性,亲子版小红车的后座,选择采用无缝钢管。
这些公共服务的概念,有时候仅仅只是为了改变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舒适度体验。
各种细节,都似乎在提示小红车超长生命周期的唯一中心:读懂人。但一辆自行车如何能够看到全杭州人的需求?真相往往很简单:它的背后,有更多愿意为公共自行车事业付出的人。
红
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的人,穿着红色的厚外套,这是冬天或初春去点位值班的工作服。
夏天,这件厚外套就会变成红T恤或者红马甲,金根胜告诉我:“红色能让市民认出我们来。”因为小红车,也是红色。
小红车服务员张亚娟的红外套,一穿就是17年。作为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对外招聘进来的第一批员工,17年里她一直坚持着一套时间表。
早上7点,张亚娟会带着统一配备的工具包,准时出现在所管片区的小红车点位上。一天里,她要负责巡查20到30个点位。
如果车架太空,她就把车“上”到架子上,以便客人扫码或刷卡借走,如果架子太满,她就得卸下来一些自行车,以便客人还车。而后,她要一个一个检查止锁器好坏,并清洁小红车。
于是,张亚娟的工具包里常备用来铲牛皮癣的铲刀、抹布、站务日记和用以标记问题车辆的标签纸。“以前标配的工具包里还有扳手,因为以前车座子是用螺丝固定的,客人没法自己调节车座高低,我们就带着扳手,随时可以帮忙调。”
遇到打气、调试刹车等需要小修的车辆,张亚娟或巡点的维修工会带着小零件,以便顺手就在路上修好。“如果要做深度修理,基地车会沿路把故障车收回基地,修复检测好后再投放出来。”周霏强进一步解释。
从人流量最大的点位出发,绕一圈,晚上7点又回到初始点位打卡,其间还要临时处理各种突发状况。有时调度中心一通电话打来,张亚娟就要立马出发前往问题点位,饭也顾不上吃。
许多小红车一线服务员,都是如此度过一天。
身为干部的周霏强和金根胜同样熟知这套流程,因为他们也要到人流量大的小红车点位上值班,加强人力。“双休日可能重点在景区,工作日肯定是地铁站和小区周边。”周霏强说,每个小红车点位的具体情况也不同,它们有各自的高峰时间,人力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配。
对于金根胜来说,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小红车,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,遇上称赞小红车的游客,他总要拜托对方,“能不能在社交平台上发一下小红车或者点赞一下,我每次都要这样说。”
有时“劝架”会变成金根胜的工作内容之一,比如在少年宫。“往往是一辆亲子车来,有三四个人在抢,还吵架,我们就只能劝一下,说按照先来后到的规则借车。也有人向我们表示不满意,说亲子版的小红车投得太少了。”
但具体在哪个点位,投放多少辆,什么版本的小红车,并非一件可以简单决定的事。因为钢制后座的存在,亲子版小红车要远重于普通版小红车,骑行舒适度因此稍差,受众范围集中在带小孩或带重物的使用者。“正常情况下,肯定是普通版小红车更多人骑。”金根胜说道。
对于小红车工作人员来说,他们则需要考量,到底要把亲子版小红车的投放量控制在什么范围内,才能平衡普通骑行者与有娃骑行者的需求。过去这更多靠一线积攒起来的经验,现在可是一个技术活。
活
在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一楼,有一个巨大的屏幕,用以显示全市所有小红车点位的具体情况。
监控平台可看到包括在架车辆数、待维修车辆数、骑行中车辆数、车辆周转率、扫码注册量和碳排放数据等,数据都是5分钟更新一次。点开具体的运营点位,还可以看到该点位的待维修和待保养车辆数。
这套系统,是小红车工作人员掌握“全局”的关键工具。通过不同数据的对比,他们将得以确定,如何投放小红车,如何派遣工作人员能更贴合需求。
此外,他们会通过收拢各个渠道的消费者意见,对小红车和服务进行优化。
周霏强坦言,小红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,就是小红车点位的有限性、布局的固定性和城市发展、市民需求变化之间的矛盾。“还车难”矛盾一直存在。
但为了城市有序化管理,小红车暂时无法放弃固定“点位”,无法采取和共享单车一样随用随还的模式。
在纷至沓来的改进意见里,小红车最终捋出了一条线,在2016年开启了扫码租车,2021年推出了免押金租车,2022年开始推广电子围栏。到2025年,小红车已经更新至第六代。
摸索,然后改进,因为需求才是公共产品小红车“活着”的根基。而杭州,也需要小红车,以平衡城市里收费越来越高的共享单车。为了“活”下去,小红车和杭州,都最大程度地活泛起来。
在最初的规划里,杭州把一部分市政道路免费“出让”给小红车这个公共产品,并由政府投资建设小红车所需要的亭、棚,“后续运营方面的费用就由我们自己来负责”,周霏强告诉我。彼时,小红车就是这么在毫无国内先例的情况下,运转起来的。
在2019年财政退出小红车项目之后,周霏强才真切感受到“顶层建设”的重要性。一个定位为公共产品的公益项目,如果没有财政支持,要怎么运转下去?
杭州似乎在走第一步的时候,就已经想到了五步之后。正如2002年,杭州取消西湖门票,把西湖变成全国第一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5A级景区的决定—“还湖于民”的想法曾遭人诟病,结果却表明,失去了2000多万元门票收入的西湖,反而直接拉动了景区周围更多消费。
“当初顶层设计时就很明确了,小红车定位为公益项目,占道是免费的。政府提供政策资源,但不是一味地投入钱,它要求企业自己去运作起来。如果都是财政兜底,总有一天这个水池要被抽干。”周霏强认为,好在杭州从一开始就给小红车留了一条路。这条路在具体项目里,就是小红车早期建设时的亭棚。
亭棚的存在,让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在2019年后,拥有了资源开发的可能。“在推广无人值守之后,这些闲置的亭棚就可以通过国有资产挂牌的形式,做一些类似于报刊亭、售卖亭的销售点位,这几年我们基本上维持收支平衡。”周霏强觉得,恰是因为政府前期规划时,设想到了需要企业自运转的结果,才能有小红车实现自我造血的空间。
“服务出让”,是小红车的另外一次尝试。在其他区域按需建好公共自行车设施后,他们来辅助运营,根据不同合作模式收取相应费用。这个合作模式之下,各区车辆互通,小红车的规模变得更大。
从周霏强的角度来看,好处还在于规模效应能够更大发挥作用,“如果点位少,市民难借难还,就不爱用了”。
在2019年后,尽管政府不再直接拨款至小红车项目上,但杭州小红车公司与杭州市政府的“合作”仍然存在。在新的建设模式中,新的楼盘、学校需要按照政府规划同步建设小红车点位。
“开发商有政策,非机动车位需要拿出一部分来配给公共自行车,这个原本政府要出的建设资金,就由开发商来出,但相应的是,开发商可以冲减一部分非机动车位。寸土寸金,开发商也有利。”周霏强解释了现行三方平衡的“配建”模式。
许多努力和配合做出来,小红车才得以被放进并留在杭州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。
变
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公共产品定位,意味着小红车点位的布局需要随着出行格局的变化而变化。
在小红车刚面世的2008年,杭州地铁尚未开通,市民出行多依赖公交。杭州市政府将公共自行车项目“交付”给杭州公交集团牵头做,为的就是把公共自行车作为一环,纳入城市交通体系。因此,在2009年主城区小红车点位布局基本成型时,其点位大多随着公交站布局。
然而,在2012年,杭州开通第一条地铁时,小红车发现自己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:地铁衔接问题。
“地铁开通之后,杭州市公共交通出行的格局完全被打破,我们也是慢慢在地铁周边建了点位,但是也碰到一些问题,一个是地铁周边寸土寸金,另外地铁人流量和公交人流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,高峰时段地铁一个站会出来几百人,瞬间就不够用。”周霏强也为此感到有压力。
两者相比,人流量大所带来的矛盾似乎更好缓解,小红车已经开启无桩电子围栏时代,在同一个给定的市政道路范围内,能够停放更多的车辆以供使用。但占地问题,却是两难。
因电动自行车的摆放整理问题都没有解决,小红车的租还车区域更加无法靠近地铁。目前小红车只能选择折中,有条件的情况下,在距离地铁口两三百米处配建点位。
一项公共事业要在城市落地,总是面临千头万绪。最实际的问题,依然是离了财政后的“自我造血”的问题。
“也曾有市民建议过,你们也可以适当收点费,共享单车是1.5元,你们收5毛钱。后来这也被我们否决了,因为说起来我们的初心就是免费。公共自行车的属性,是公共产品,相较于经济效应,更注重社会效益。”周霏强说道。
费尽千般力气,小红车在维持98%免费率的情况下,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,但想做的仍有很多,比如更新车辆,更大范围地推广无桩车。这些,都需要更多的营业收入来支撑。
杭州不是一座百分百满分的城市,小红车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公共自行车项目。它们最终能够闯进更多人的视线,靠的是一种“先试一试”的勇气。
2025年,小红车想要再试着走一次用碳交易实现自我造血的道路。这条路注定是艰难的,业内唯一一个成功者,就是2012年的小红车,但过去几年,小红车再次被立项问题卡住。
目前中国的碳交易尚未完全成型,被纳入碳市场的行业主要还是碳排放量较大的发电行业、高耗能的钢铁、建材行业等等。而体量较小的公共自行车行业,还没有被系统地纳入市场。
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2025年要“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”;浙江省也出台了新的减排政策,“虽然还不确定小红车是否符合申报标准,但是我们把(碳减排)的数据都先留了下来”,周霏强说道。
无论如何,再试试吧。能够点石成金的“贤者之石”,永远藏在下一个实验步骤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