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年,谭琳和儿子在北京百望山森林公园
胡洋洋摸着墙壁从厨房走回卧室,一拐弯,撞上了我。
“哎呀,对不起。”男孩小声说。他摸到我的手臂,下意识地侧身避让,我才发现自己挡住了路,急忙伸手去扶他。
胡洋洋14岁,先天性视力障碍,全盲。他个子小小,嗓音清亮,俨然还是个小男孩的模样,看不出已经是个初三学生。
但他不在盲校读书,而是在普通学校上学,和健全小孩一起听课、玩耍,应对考试,从小学一年级一路读到初二。
EYE加倍中国视障儿童教育发展项目负责人谭琳告诉南风窗,她曾负责统计全国普校教材盲文版的征订,根据征订数字不完全估算,像胡洋洋这样,在普通学校读书的全盲儿童,全中国“可能不超过20人”。
今年9月1日,人数再减去了一位。
因为升上初三,胡洋洋结束8年的普通学校教育生涯,正式转入盲人学校。
盲生在普校读书,这条介于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路径,被称作“融合教育”。国际上,它还有个名字,叫“全纳性教育”。这名称背后的教育理念是,没有歧视,没有分类,学校要接纳所有儿童,给予他们平等的受教育机会。
长久以来,我们习惯了为身心残疾的学生设立特殊学校,进行专门教育来满足特殊儿童的教育需求,但同时,有意或无意地,在残疾儿童与普通儿童之间砌起了一座高墙。
融合教育旨在拆掉这堵墙。
我国自1986年起就有明文规定,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备“适应进校学习能力”的残障儿童。2017年,《残疾人教育条令》修订,强调要积极推进融合教育;2020年,教育部出台《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要求完善随班就读工作机制,提升随班就读工作水平。
一年一年,政策愈发完善,呼声愈发高涨。但落至个体,视力障碍儿童,特别是全盲的孩子,想迈进普通学校的大门,仍然是种奢望,机会渺茫。
初秋,刚下过绵绵细雨,第一轮降温已经来了,蝉鸣却仍然聒噪不停。胡洋洋在卧室里上盲校的网课,他的妈妈闫湘坐在厨房餐桌旁,声音很轻,有些落寞。
她说,对这个结果,“我们都挺沮丧的”。
跳出来
他们为什么送一个眼盲的孩子去普通学校读书?
每年夏天,全中国有1000万学生参加高考。这场考试是人才选拔系统里运转效率惊人的大型枢纽,它将集中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分配给孩子们。全中国各地的1272所大学、717种不同专业,向普通高考生敞开怀抱。
但在盲校的升学路径里,多数孩子的选择,少得可怜。
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后,一些盲生直接升去职业中专,学习方向基本一样:推拿按摩。
成绩还不错的学生,有机会升上盲校高中,参加面向视障学生的单独高考。2021年,全国在特殊教育高中就读的盲生一共1761人,面向他们的招生院校有四所:长春大学、北京联合大学、滨州医学院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。专业则只有两种:推拿按摩和心理学。还有个别学器乐的孩子可以去读音乐学校。
此外,基本没有更多的选择。
都是学生,“早上八九点的太阳”,但普通学生与视障小孩,道路之宽窄,天差地别。
陪着儿子求医求学这些年,闫湘接触的视障人士,几乎全在从事推拿按摩,“生活被规定下来,一眼望得见头”。
推拿按摩好就业,上手快,工作环境安稳。在视障人士的就业选择没有得到拓宽之前,推拿按摩将一直是他们最稳妥的出路,是盲校教育的主流。从小,视障孩子就被有意无意地推着往这条路上走。
可总有人不愿意随主流。
生活在天津的刘明硕14岁,个头已长到一米八。妈妈李春花是个典型的北方女人,热情爽朗,一口地道的天津话。
妈妈讲话时,明硕就乖巧地坐在一旁听,很安静。他得的是一种基因突变的罕见病,先天性黑蒙,双眼视力只有0.02—0.04,需要把脸贴在书本上,才辨得清文字。在他看到的画面里,世界是由一堆模糊的色块组成的。
明硕看起来内敛,不善言辞,但妈妈说,儿子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。他很坚定,不想去学推拿。
为向我印证这点,李春花转过头去问他:“你以后愿意学不?”
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明硕很干脆地回答:“不愿意。”
“他不想学。”李春花又看向我,重复了一遍儿子的话,继续说,“他昨天还和我说,想走出天津,去外地上大学。”
对于不愿意被推着走上这条路的孩子而言,选择有两种。一是被动等待,等待盲生教育体制和就业环境的改变,这需要耐心,和一段漫长的时间。二是从传统体制里跳出来,自寻出路。
孩子一天天长大,一些父母不甘心再悲观地等下去了。
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点鼓励,便带着孩子,试着闯进普通学校里。他们希望孩子像个普通小孩一样入学、读书,参与中高考,去争取接受各种教育、职业训练的机会。
谭琳的儿子也是视力障碍。2008年孩子诞生后,她就辞去了工作,全身心扑在孩子的教育上。2019年,她去往台湾读研,学习特殊教育。她想寻找一种解法,寻找一条让视障儿童走出个人发展窘境的通路。
在那里,谭琳亲眼看到,一所小学里,24个视障小孩坐在普通学校的教室里,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。那个场景震惊了她。
视障小孩的教育原来不止特殊学校一种,他们还可以自愿选择去普通学校读书。学校里,有资源老师去支持这些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,在普通学校、特殊学校和家庭之间协调沟通,配备学习所需的材料和辅具,甚至坐在孩子旁边一起上课,将任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什么、画了什么描述给孩子听。
而这,就是人们一直听说的“融合教育”。
“疯狂”妈妈
闫湘决心为了孩子,搏一把。
她不忍心让儿子去干按摩。胡洋洋发育得较晚,个子和力气比同龄人差上一截,和同学站在一起,就像小学生混进了成年人里。如果干按摩,肯定很辛苦。
洋洋虽然看不见,但心智健全,从小就表现出机敏的一面,6岁时去上盲校幼儿园,和大自己一两岁的孩子一起学盲文,学得快、记得牢,老师夸他聪明。
是当时的盲校老师鼓励闫湘,让洋洋从盲校幼儿园毕业后,改去普通小学读书。
那年,洋洋所在的盲校正推行“随班就读”的融合教育项目,和洋洋一起被推荐去普通小学念书的,一共有三四个孩子。
盲校老师们的理由很简单:由于视障学生个体差异较大,为适应孩子的平均能力,盲校所用的教材删去了一些重要内容,教学标准相比普通学校来说,有所降低。这样日积月累,他们看到盲生与普通学生在学习能力上,逐渐拉开差距。但其实,有一定比例的盲生,是无法被盲校教材“喂饱”的,他们有能力去普通学校尝试“随班就读”。
所以,个别时期、个别地方,盲校老师会建议有能力的孩子去普校上学。
就这样,7岁的洋洋,早早走上了融合教育的道路。平日在普通学校读书,时不时去盲校借书、打印盲文学习资料,盲校的资源中心老师还推荐他去学习了盲文电脑。他的小学六年过得比较顺利,成绩也一直不错。
但2020年9月,困难来了。这本是胡洋洋从普通小学毕业、按理该升上初中的时候,然而,在南京市内,怎么也找不到一所愿意接收的中学。
其他学生按时开学了,洋洋还没有学上。焦虑的闫湘就领着儿子去教育局找人询问,他们便在大厅坐着,从早上开门,一直待到中午,天天如此。
先是中学教育科有人来和她沟通,然后是小学教育科,最后是局长本人。终于,教育局决定举行一场鉴定会,请来数位特殊教育学校的高级教师和教育专家,现场对孩子的视力和学习情况进行评估。
闫湘用“舌战群雄”四个字形容那场鉴定会。
“反正咬死一句话,不同意,你说什么我都不同意。”她当过几年中学语文老师,孩子降生后就天天和他待在一起,她看得见孩子在普校的成长,认为自己“清楚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”。
洋洋刚上小学时,学校有调皮的孩子,喊洋洋“小瞎子”,捉弄他,把他反锁在空教室里。后来一次无意中,洋洋给同学们讲历史和武侠故事,用好记忆力和口才,在学校慢慢拥有了“粉丝”,成功扭转了同学对自己的态度,从“小瞎子”变成同学口中“会讲故事的人”。
中午,洋洋还在吃饭,宿舍里就有“粉丝”在等他开讲。有时,体育课因为天气原因上不了,老师也会让洋洋来讲台上朗诵。
前年,洋洋学会了用电脑,开始在网上聊天、打游戏和听小说。闫湘有了青春期男孩儿妈妈的共同苦恼,需要三令五申地限制小孩打游戏的时间,甚至半夜起来“查岗”。这过程中,让她觉得神奇的是,儿子和普通学校的同学一起打游戏,竟然被喊“大神”,被要求提供攻略。“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。”
来自其他孩子的认可,让洋洋慢慢建立起信心和目标,想成为一名主持人或者主播。
而这整个过程,作为妈妈的闫湘都看在眼里。她亲眼见到自己的儿子,小小年纪,却凭借自己的能力,赢得了普通小孩的认可和尊重。这是她在许多成年视障群体身上都没有见到过的希望,无比珍贵,却又无比脆弱。
再退一步说,“小学六年,洋洋没出过什么安全事故,成绩也跟得上,为什么初中就不让继续读了?”闫湘想不明白。
但最后,2020年9月那场鉴定会的专家鉴定结果是:胡洋洋不适合进入普通初中就读。
一股蛮劲儿支配了母亲闫湘。她不服,拒绝在鉴定结果上签字,反而继续去大厅静坐。
终于,开学半个月后,胡洋洋有了一个在普通初中试读的机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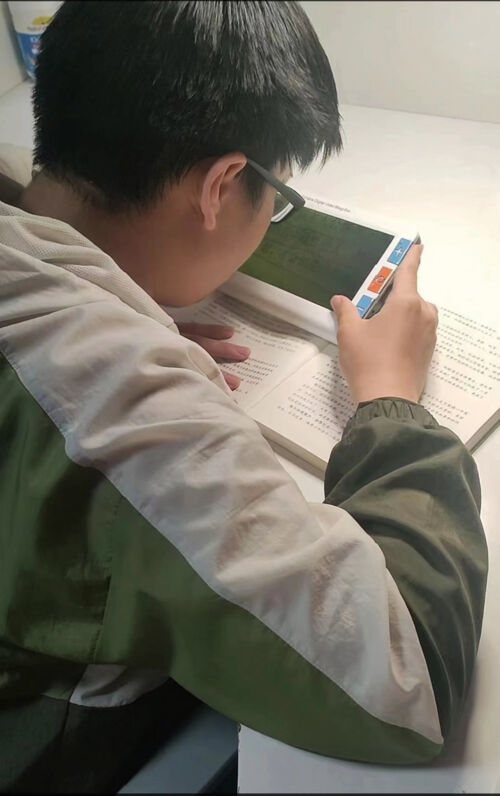
刘明硕需要使用助视器才能清文字,他的课本是放大字号的翻印版
匮乏的支持体系
更大的难题,还等在后面。
北京爱百福视障人士关爱中心负责人曲老师说,在如今缺乏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情况下,普通初中的课程难度,对盲生实在太大了。特别是数理化上,盲生有天然的理解限制,“很难和普通孩子比拼”。
在胡洋洋的求学之路上,数学几何是头凶恶的拦路虎。
对于半途失明、看见过方、圆、空间的孩子,几何的理解门槛还稍低一些,可洋洋生下来就看不见,缺乏基本的视觉概念,学起来难上加难。
闫湘自制了一块板子,用图钉和绳子来表示点和线,摆成和题目对应的三角形、平行四边形,让洋洋摸着学。
然而,这块朴素的、凝结着妈妈心血的板子,教学效果不太如意。
曲老师曾去美国开展融合教育的普通学校参观交流,在那里,盲校配有3D打印设备,可以把数学、物理、地理课本上的立体图形,打印成微缩的立体模型,让学生们通过触摸,感受、理解、快速掌握。
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学校都没有这种支持。“视障孩子要怎么去学几何?确实不容易。”她说。
爱百福中心帮扶的一些视障孤儿,在被美国、法国家庭收养后,仍然与曲老师保持着联络。曲老师从孩子们的求学经历中发觉,欧美那套融合教育的路径,根植在他们国家教育系统、福利体系和社会观念之中,很难将其剥离出特定环境,直接复制到中国的土壤上。
还有,国外学业相对轻松,对特殊儿童更友好。中国是应试化教育,知识难度大,升学竞争激烈,也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。
普通学生尚且被压得喘不过气,何况对于视力障碍的孩子?
“还是要从方方面面来考量,走一条中国之路。”曲老师说。
原人大代表袁敬华是山东夏津特殊教育学校校长,数次在两会上为残障儿童的教育问题发声。她觉得,应该建立一个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,评估残障孩子是否适合融合教育,普通学校是否有条件接收。否则,不适合的融合教育,只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。
接受媒体采访时,袁敬华简单举了个例子:她曾收过一个聋哑学生,经过训练,上完幼儿园大班进入普通学校就读,不到半年,言语表达退化,又回到了特殊学校。
“不能让孩子随班就读变成‘随班就蹲’。”她说。
2020年,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言人在就《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答记者问时承认,现在随班教育工作整体水平不高,问题突出,其中一点就是随班就读的资源保障条件不完善,对随班就读孩子的专业支撑作用有限。普通学校缺乏对特殊教育需求学生的针对性辅导,这会影响他们的学习质量。
由于这种支持的匮乏,勉强坚持读完初二后,洋洋很难再跟上普校的学习进度了。
他文科学得还不错,能在班里排得到中等,就是理科学习一直没有找到解法,严重拖后腿。中考竞争激烈,高中升学率只有50%,继续在普校学下去,即使参加了中考,他的成绩也“很难考上高中”。
“权衡一下,还是选择到盲校去了。”
闫湘说着,一边抚摸着那块几何板子。她顺手把彩色图钉拼成一个等边三角形,放在一旁。
站在一起的妈妈们
有时,就连最亲密的家人,都不理解闫湘。
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,说她自私、不切实际,让盲孩子去普通学校读书,只是为了“作为家长的自己脸上有光”。
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她就和其他视障孩子的妈妈打语音电话,聊孩子近况,在学校里的境遇,还有去教育部门“闹”所吃下的苦,一聊就是几个小时。
盲孩妈妈们,彼此分享盲文教材和教学资料,分享自己走过的弯路和可行的解决方法,慢慢地,建立起一个小型的互助社群。
开学前,李春花对于要不要支持明硕继续在普校读书,有些动摇。儿子的近视比之前又长了200度,医生叮嘱他们要合理用眼,这么下去,视力可能会继续下降。
可是在普校读书,避免不了用眼的过度。读初二时,明硕每晚用助视器写作业就要两个半小时,从七点半到十点。再往后走,学业压力只升不降。
当地残联的人也劝李春花,虽然政策文件写着支持融合教育,但站在务实的角度,即使在普校读完高中和大学,将来就业也会有限制,不如尽快去盲校选择适合孩子就业的专业方向—当然,很大概率是推拿按摩。
辗转反侧好几夜,李春花给谭琳发了一条信息。
谭琳想了很久,回复她:“20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残障者不用学习,50年前,美国还给智障者做绝育手术。如果每个人都面对现实就‘认了’,那人类的文明就永远停止在远古时代。正是因为有勇于打破刻板印象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去吃螃蟹,才让社会对残障者的态度和接纳程度越来越开放。”
李春花回想起儿子刚诊断出视力障碍时,她压根没想过儿子能去普通小学读书。儿子上小学时,没想过能上普通初中,但还是一步步走到现在了,那么苦,也收获那么多。
“就这么去盲校了,确实不甘心。”
今年6月,为了让明硕顺利参加初中会考,李春花向天津市考试院申请提供残疾人合理便利,允许明硕考试时携带助视器,延长30%的作答时间。
几经周折,最终成功了。
明硕成为了天津市第一位申请到中考合理便利的视力障碍学生。
儿子能继续读书,还有条件参加升学考试,一直悬在李春花心上的那块石头落了地。紧接着,她又想:“我们开创了先例,以后,天津市其他视障孩子也有希望参加会考和中考了。”
李春花把自己申请合理便利的经历写下来,整理了全国各地残障考生合理便利政策的相关文件和申请表格,想分享给其他视障孩子的父母。谭琳给这篇文章起了一个标题:普校里的孤勇者。
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合伙人蔡聪,是视障公益圈中的名人,参加过《奇葩说》,在综艺节目上倡导残障人士的融合。蔡聪曾写道,目前,视障学生参加普通高考的专业选择、就业出路、教育路径,尚且处于摸索阶段,这种情况下,还愿意去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学生,“确实需要一些向风车发起冲锋的浪漫主义情怀”。
闫湘和我讲了一个令她难以忘怀的事。2019年,一位通过普通高考被大学录取的盲人去报考一所盲校的教师岗位,笔试和面试的总成绩名列第一,却因为视力达不到体检标准落选。盲人学校不招收盲人当老师,诸如此类的怪象,在视障群体的升学与求职过程中,比比皆是。
人们常把残障看作一种缺陷,认为它是残障人士相对于健全人的能力缺乏与功能限制。但其实,“残障人所遭遇的困难不是残障导致的,是不健康的社会态度与政策,共同造成了对残障人的社会排斥与隔离”。
需要有人去撼动这庞大而坚固的社会观念,“否则永远没法打破怪圈”,谭琳说。
她们决心携起手来。
(文中胡洋洋、闫湘为化名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