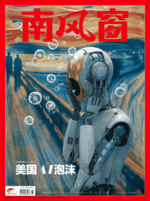中国科学院院士颜宁(受访者供图)
“成为女科学家的道路或许充满挑战,但还不足以阻碍你前行的脚步。所以,请勇敢做自己。”
5月末,第26届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揭晓,颜宁成为该奖项创办以来第8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。她在颁奖典礼上,舒缓且自信地说了上述感言。
这位47岁的女科学家,被许多人认为是“天才少女”般的存在。1996年考上清华,接着在普林斯顿大学师从施一公,研究更微观的结构生物学。2007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毕业,接着便是一系列的“最”,30岁,她成为清华最年轻博导;37岁率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,攻克50年来最受瞩目的膜转运蛋白难题。
很多次的合照中,颜宁是报告厅里罕见的女性。无论年龄还是性别,属于“少数派”的颜宁被认为是触不可及的天才。只有天才女性才能攀上世界高峰,“战胜”男性,成为焦点……许多人这么告诉女孩们。
颜宁不是这么想的。早在2014年,她发现,女性在博士、博士后的阶段表现都很棒,却在进一步的学术生涯中失去了姓名。她想知道,女科学家去哪儿了?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?
于是, 她在繁忙的科研中,抽空办论坛、参加活动,做本不属于她职业范畴的事。数位受访女学者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,颜宁是她们的偶像,是能真切激励她们往前走的人。因为看到颜宁的存在,西湖大学博士后孙耀庭说:“我想努力地做好我自己。”
而普通家庭出身的颜宁,尽管屡次荣誉加身,也从未改变内心。她仍追求最简单与纯粹的进步。这股力量助她成为外人眼里顶尖的科学家,接着用这股劲告诉所有人,当女性成为自己,可以有多美好。
穿平底鞋领奖
47岁的颜宁,已经很久没有主动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了。
2022年,她离开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教职,回到国内,在从未待过的南方,成为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。2023年,她又担任了深圳湾实验室主任。
工作内容变得愈加复杂,白天,她要像普通白领一样,上8小时的班,处理行政事务。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夜晚,属于她的科研时间才开始。
每天的时间变得愈加不够用。颜宁的理论是,睡眠不是按天来算的,而是按周计算,“到周末我能睡12个小时,我觉得这就是挺幸福的一件事”。为了挤出更多的科研时间,她谢绝了许多应酬与外界的关注。
但在2024年5月末,颜宁还是参加了第26届“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”颁奖典礼。她成为全球350位候选人中选出的5位杰出女科学家之一。5月29日,她在巴黎发表了一段4分钟的演讲。
她在颁奖后的群访场合解释,之所以愿意出席领奖,是因为过往的女性前辈让她相信榜样的力量。那就是,“(如果)你知道有人曾走过这条路,就不会太害怕”。她会坚定地走自己想走的路。
她的人生轨迹,也给别人展示了忠于自己的魅力。她每天待在学校,不知疲倦地与学生和科研为伴。她的博士后学生潘孝敬曾形容,颜宁免除了许多世俗意义上的烦恼。“跟她在一起对比的时候,会觉得她是个小孩,而我真的是年纪好大。”
她那拥有120多万粉丝、但是没加大V标志的微博,也说明了这一切。科研之外,颜宁喜欢发微博追星、关心时事、分享生活。她自称,要在微博“做没心没肺胡乱作妖的混世魔王”,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。
新冠大流行期间,她关心中美防疫政策,为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发声。她同时在意女性困境的方方面面,包括身材焦虑、容貌焦虑、成为母亲,甚至“相亲是否要AA制”等小事。
有好几次,她发微博“警告”,凡对她的外貌评头品足者,“不论善意与否,被我看到一概删黑”。
她接着解释,“女应为己容”。“化不化妆、如何穿戴全凭心情,关外人何事?约定俗成的所谓‘得体合宜’的妆容就对么?这是否也造成某种程度的职场不公呢?如果不以愉己为目的,那不是徒增工作成本么?”
一些人质疑她的强势。近日,她在受访时被问及“为何做了院长并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,减少发微博的频率”,再度给出了“做自己”的答案。
“发微博对我来说是个休闲,让我改掉会很难受……我也是第一次做院长,有时候还很任性,不按常理出牌,但我有我的风格,大家习惯就好。”
比起照顾众人的看法,她更愿意“纵容”自己的任性。
5月末,在巴黎领“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”,颜宁听从了侄女的建议,穿了平底鞋上台。
惊喜随之而来。她又发了条微博:“一个小观察:获奖(女)人们都穿着让自己舒服的平底鞋或半跟鞋,不委屈自己[嘻嘻]要感谢的人委实太多,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谢谢你们给我勇气、力量和信心。”
“冷门赛道”
颜宁曾回忆,上本科时,她是疯丫头,并未想过走上科研道路,最终成为女科学家。
兴许是天赋与幸运相融的化学反应,2000年,颜宁到普林斯顿大学硕博连读,第二年成为施一公第一批中国弟子之一,研究癌症相关的凋亡通路。在世界顶级学府,颜宁感受到了巨大的同辈压力。她不分昼夜地读论文,每天只睡六小时,睡前拿着论文集,睡醒了接着埋头读。
施一公的严格要求曾让颜宁深感绝望。她形容这段时光简直 “暗无天日”,“(当时)我是做什么,什么做不出来”。到了在普林斯顿第三年,她迎来一生都在铭记的日子。
2003年1月11日,施一公告诉她,“你终于会做实验了”。经过漫长的试错与反复练习,她第一次成功做出了复杂的实验。成果带来的欣喜不止停留在颜宁个人。施一公在离开普林斯顿后回溯,那么多年来,他实验室里4个最好的生化实验,其中之一就是颜宁那次做的。
外界很难想象一次成功的实验对一个苦于证明自己的博士生的激励。2019年,在颜宁组织的女科学家论坛上,她透露,跟从施一公的训练带给她成就感,让她决意走上科研道路,并为此越陷越深。
博士后期间,她选择了一条学术圈冷门的领域—膜蛋白。这是关于人体细胞膜分子层面的研究,大分子甚至某些小分子进出细胞膜,需要经过膜蛋白。
唯一的问题是,膜蛋白在学界众所周知地难,研究者寥寥。
颜宁忘不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说的话。2002年,王晓东来普林斯顿交流时曾说,癌症领域一半人都在研究p53(注:肿瘤抑制蛋白),“不是因为p53更重要,而是因为研究的人多”。
“这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。当时我就觉得,不要去做太热的东西,要尽量去找一些别人没注意到的,这才是真正的金矿所在。”颜宁说。

2024年5月28日,“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”颁奖典礼在巴黎举办,颜宁发表获奖感言(受访者供图)
最重要的事
颜宁接下来的成功众人皆知:她发现了膜蛋白领域能被写入教科书的成就。进展在这之前有些前兆了:2006年,颜宁成为清华最年轻的博导以后,很快在4年间带领团队解析了5个膜蛋白结构。于是,2013年,她打算转向研究膜蛋白领域的“皇冠”—困扰科学界50余年的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。
身边有博士生为此与她争论了很久,认为这个研究转向有些“一步登天”。但颜宁的一往无前在于,对目标的强烈渴望让她愿意承受所有的代价。
《成为科学家》一书披露,颜宁当时对反对的学生说:“你已经做到了这个程度,不缺一两篇《自然》或者《科学》的论文,我不在乎,你也不应该那么在乎。你现在有时间、有精力,还有财力去做一件事情,为什么要去做那个次等的,而不是最重要的?”
这样的疑问伴随着颜宁的职业生涯。2023年,她的一条微博引起了很多人感叹。她在面试博士推免生时,提了同一个问题:假设时间来到10年后,你成为一名PI(独立带领实验室的博导),拥有无限的资源与团队,你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?
她对学生的答案感到失望。近一半的同学诚实地表示,现阶段还没想过这种问题;有的同学讲了文献里特别具体的小问题;有的同学泛泛地说一些感兴趣的领域……
而她更想让选择深造的同学,相信导师施一公告诉她的,“dream big & aim high(目光远大)”。“没必要只到文献里寻找你的科学问题,也不要总是循着你之前PhD或博后实验室的方向、套路走下去……人类的知识才多一点儿啊,那么多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呢。”
在多次受访时,她也曾表露,做科研对她不是负担,而是很好玩的事情。
这种好玩体现在,成为“世界第一人”。
“你是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在不断地往前推动。当你能够得到一个答案,只要别人没有发表,你就是第一个知道答案的人,就有一种我是在代表人类的观念。这是我很喜欢的成就感。”她说。
2022 年,她从普林斯顿大学回国,对学生们的要求也是相似的。“我跟我实验室的博士后、博士们都说,我们Yan Lab有我们自己的标志性课题,就是过去十几、二十几年要做的课题上还有哪些没有完成的,必然要把它做出来。”她近日接受采访时透露。
她同时也是尊重学生自由选择的老师。“博士后可能觉得,(如果做太难的课题)我将来找不着工作怎么办?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矛盾。所以我跟他们说,如果你觉得必须要有这种好文章你才好往前走的话,那我支持你去做这个课题。这么一段时间试验下来,我觉得结果挺好,大家反而更有动力了。”
2014年春节前夕,获取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三维结构的那个冬日夜晚,就是如此。这项成果于2014年6月5日在《自然》发表,颜宁第二年同时获得国际蛋白质学会“青年科学家奖”和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。
颜宁回忆,整个过程,她的成就感爆棚,原因在于她再度挑战了人类认知的极限。
“我是喜欢纯粹的,”多年后,她在微博上写,“看体育就单纯地看谁能突破人类的体能和技巧极限;做科研就看谁能突破人类的智力极限……世界当然不简单,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把一些事情简化,纯粹地去享受那一瞬间。”
随着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明,结构分子学界欢欣鼓舞,追求极限的颜宁却陷入迷茫。这意味着,大分子复合体的结构可以直接用冷冻电子显微镜进行解析,过去最难的一步“结晶”已经难度骤减。
眼前的路,当它太轻易实现时,就变得狭窄且无趣了。她在2014年的年终总结中写道,“日新月异的各种新技术新领域,我反而变得不知道何去何从。不止一位前辈教导我:不要总妄想进入新的领域;他们还会列举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得奖之后想做新鲜好玩的,却往往折戟沉沙,再无佳作问世。(2015年)跨年,我的状态是迷茫。”
5比5
迷茫的颜宁,没有放弃在结构分子世界寻找“好玩的”。她说,最近她感兴趣糖类、脂类的生命暗物质和化学领域。给实验室招生时,她也偏爱跨学科的人。
造成这一转变的主因还是因为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。在技术的加持下,颜宁解释,结构生物学从一个需要结晶的验证性的学科,变成了一个发现新物质的学科。
她逐渐享受探索未知边界的过程。 “以前我做科研是有明确的目标,然后去实现它,现在的目标如果是以发现为主,我反而就跟大家说,我们做科研你要脚踩西瓜皮,从专注地去解决问题变成我去发现问题,我去问出问题。”颜宁解释。
热衷于提问的颜宁,还在着手给科研女性一些力量。她总结,人生的三个阶段,前两个是自我学习和证明自己。当完成了这些后,她想进入第三阶段—更多地输出自己、承担公共责任。
面对科研同行者和后辈,她表现出远超逻辑的共情力。她关注女科学家,起因是在2014年前后,一位女博士生告诉颜宁,自己不想再读博了,打算出去工作。
女学生的“后退”让颜宁五味杂陈,也让她开始思考造成男女科学家比例差异大的原因。她曾表示,以前刻意不就性别问题发声,“因为本身作为女性,在公众场合强调女科学家,我担心是在为自身谋求利益,似乎有违背公平竞争之嫌”。
但是等她做了教授以后,她才发现,“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她根本不是占便宜。比如说我的一个学生她生了孩子,像泵奶这种事,你就必须得找个地方,对这些没有办公室的博士、博士后们来说,这是不是就是事儿?好多地方都没有母婴室,还得去臭烘烘的卫生间。所以自从意识到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是有很多需要公平的地方后,我才开始关注这个话题的”。
2015年起,她在清华大学发起“女科学家论坛”,每年请大量女学者,讲出她们的经验和困扰。
话语是温柔且坚韧的。她在2019年的论坛上说:“大家都知道,我很不喜欢的一个问题,是问我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,我不喜欢回答,因为这不是女性的问题,而是两性的问题。但是今天在这个论坛上,都是可以讨论的,我们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”
看到更多女性的困境后,颜宁也愿意更多地发声。在2021年的女科学家论坛上,颜宁的一位学生说,生育后,“第一个要感谢自己的老公,因为我们的付出完全是一样一样”。
颜宁立刻说:“打扰一下,你为什么要感谢他呢?你看这是不是一种约定俗成,只要他帮忙,你就特感动?但这就是(男性)应该做的呀,你都带球跑了9个多月了,还花了50%的时间,他应该好好谢谢你。”
她的反问振聋发聩,因为她总在挑战那个被固有思维禁锢的观念。她喜欢鼓励女学生,打破惯性思维,通向属于女性自己的路。近年来她发现,女博士后愿意继续做科研的越来越多。而当更多女性留在牌桌上,隐藏在性别背后的结构性困境正在被改善。
2024年,她告诉记者,在深圳医学科学院的实验室,PI男女比例刚好5比5。“我发誓我没有特意选男女,但真的是一半一半。”
现在,我们可以向前一步。
颜宁在自己的女学生身上发现了清晰变化。刚来颜宁实验室时,这位学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独立领导实验室的PI。
“但到了我实验室之后,看到那么多女性,包括我,她就会觉得,why not me?我怎么就不行了?所以你在一个特别好的环境里面,就会让人获得自信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颜宁说。
6月,她又着手准备一年一度女科学家论坛。这一次,论坛的子话题之一是:如何培养女性领导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