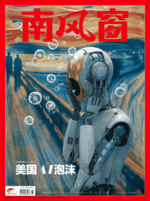黄耀祥院士
中国稻作界,有一片江湖,流传着“南帝、北丐、东邪、西毒、中神通”的传说。
最为国人熟悉的“中国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,被称为“中神通”,而“南帝”指的是矮化育种专家、广东省农科院的黄耀祥院士,“东邪”是福建省农科院院长谢华安,“西毒”是四川农业大学教授周开达院士,“北丐”是杨守仁教授。
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,是关于“南帝”黄耀祥。
黄耀祥何许人也?
这要从一场台风开始说起。
1953年,台风过境,广州城内到处湿漉漉,一片狼藉。
稻田里,原本在高产栽培试验中被寄予了“好禾”厚望的“广场13号”稻田,全倒了。
面对这伏倒的稻田,黄耀祥很是失落。当时,正是他刚回到农业科研田野的第五年,他已带领育种小组选育了“江南1224”“广场13号”品种,在广东省农业试验场参与育种工作,小有成就。
谁知一场台风让努力几乎白费。
这是横亘在共和国初期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面前时代命题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伴随着农业生产环境的优化和施肥技术的进步,施肥带来的增产效果与作物倒伏问题之间的冲突,却逐渐显现。
那是“以粮为纲,全面发展”的年代。进入50年代中期,国家粮食安全与以重工业为建设重点相辅相成。全国上下都在紧张粮食的产量。
台风过后,眼见着稻田里倒伏的禾苗,农民和黄耀祥一同心疼起来:“多好的禾呀,全倒了,能不能搞出不怕台风的种子呢?”
稻农的话,让黄耀祥从失落的情绪转入理性思考之中,他振作起来,决意要培育出抗倒伏的品种。
此后,由一场台风刮起的,是以黄耀祥培育的“广场矮”稻种为标志的中国水稻史上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序幕。在50多年的稻作人生里,黄耀祥主导培育下的品种就有60多个,累计种植面积达115亿亩以上,为社会增产2100亿公斤。黄耀祥也因此赢得了“中国大陆半矮秆水稻之父”的美名。
荣誉加身,黄耀祥依然如农民一样朴实,他平淡地说:“人人都有饭吃,这才是我想要的。”
吃饱饭,是头等大事。这也是在山河动荡的背景下出生、成长的黄耀祥最朴素的愿望。为此,他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实现。
父亲的奶油糖
一张照片记录了黄耀祥在田间日常工作的状态。
照片里,黄耀祥将衣袖和裤管都卷了起来,左手拎着布鞋,右手拄着木棍,泥巴还粘在他脚踝至脚掌处。那是刚从田里劳作后的模样。田间的风将他花白的刘海吹向头顶,与一群年轻小伙站在一道,他依然显得神采奕奕,面带笑容。
黄耀祥在自述里回顾自己的人生时写道:“半个世纪以来,我是在和水稻种子打交道的过程中度过的,除了种子还是种子,至今满脑袋装的都是种子。”
回顾黄耀祥踏上历史舞台的过程,他在与水稻种子结缘之前,先经历了一场“弃理从农”的开场,这背后是时代赋予一名农学学子“兴国为怀”的历史使命。
1935年,入读中山大学物理系半年后,黄耀祥决定放弃。彼时,物理学受西方影响而大受关注,众多亲友奋力劝阻。但黄耀祥坚持转入“吃力不讨好”的农学系农艺专业,主攻作物遗传育种学,兼攻农林化学系土壤农化。
他在自述中形容,那是“决定一生奋斗方向关键的一年”。祖国内忧外患,农民终年辛勤不得温饱,越来越多的人漂泊海外谋生。他意识到,国事维艰,根在难得温饱。
饥饿,烙印在那一代贫苦人民的身上。1916年,黄耀祥出生于广东江门开平的一个农村。因家境贫寒,黄父远洋海外谋生,留下黄耀祥兄弟姐妹五人,由母亲靠一亩多农田拉扯大。
当时,国内稻米、小麦等主要农作物产量欠佳。黄耀祥曾回忆,种一亩水稻,平均每造(从播种到收获的一个完整过程)只收两三百斤。南方高温多湿,但水稻都是“大高个”。遇上台风暴雨,水稻严重倒伏、减产,最终,落到碗里的粮食所剩无几。
幼时的黄耀祥总盼着父亲回家,带上几颗漂洋过海的奶油糖。一颗奶油糖,勾连家乡,也在他心里埋下“读书救国”的种子。
黄耀祥记得,家乡有绿油油的禾苗和翠绿的竹林。在等待父亲回家的假期,他常和小伙伴们往竹林跑。
几个孩子搭竹屋,爬上去,又从高高的竹子溜下。爬树,捉迷藏,粘知了的乐趣,拼凑成黄耀祥的童年。
某天,日头偏西时,母亲的叫唤一声声传来。黄耀祥溜下竹屋往家赶去。未到家,远远先看到家门口聚了一行人,个个脸带笑意,好不热闹。
透过人群,只见熟悉又陌生的身影—阔别四年的父亲回来了。那是比过大年更让黄耀祥神往的日子。
那年,黄耀祥不到十岁。他记得,上一次父亲回家,母亲怀了小妹,这次家人团聚时,小妹已经四五岁。
归家的父亲看上去苍老了不少。风霜爬上他的脸庞,路途奔波的疲惫显而易见。见了他,父亲瞬间绽放笑容,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,边过问功课,边往他手里塞过一颗奶油糖。
拆开糖衣,含上一颗,甜丝丝的。数十年以后,黄耀祥接受采访说,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甜的糖。
可在口腔化开的甜蜜,怎么也消不掉他心底的苦闷。
当时,像父亲这样的华人工人在异国很常见。他们如同“牛马”被差使,低微的身份备受歧视,数年才有机会返乡。每次回家,父亲便跟几个孩子讲述在国外谋生的艰难,告诫他们读好书,唯有读书,才能救国。
如何靠读书救国?后来,黄耀祥不禁在自述中写下: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农业不兴,何来中华民族的振兴?”

黄耀祥(中)早期工作照片
“矮个子”比“大个子”抗风
中国人驯化水稻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万年之前。传统上,中国水稻被称作“农家种”,这一驯化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。由于产量较低和品种的稀少,农民在种植过程中往往受制于天气条件,这导致了收成的极度有限。
1936年,在“中国稻作学之父”丁颖的努力下,他用印度野生稻和广东栽培稻,育出了世界上第一株“千粒穗”。那沉甸甸、金灿灿的稻穗,最大一株结有1400多颗谷粒。这项成果轰动全球,也为后来发掘水稻高产潜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作为丁颖在农学院的学生之一,黄耀祥见证了这一成果诞生。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,朴素的情感化为事业心。“以农立国,振兴中华”的决心,从此埋在黄耀祥心底。
20世纪50年代之前,在南方产区的水稻种植普遍面临一个问题:高秆品种水稻只要一遇到台风暴雨天气,倒伏减产的情况就几乎无法避免。
为了实现水稻的高产,包括黄耀祥在内的不少育种人士,都选择通过提高水稻茎秆粗度和硬度来提高抗倒性。经过数年研发培育,黄耀祥培育了粗秆的“广场36号”。然而,这一次试验,依然敌不过南国台风的强劲,以失败告终。
事实证明,水稻的抗倒性与茎秆粗细并不直接相关。黄耀祥只得另取他道。
人定胜天,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在天灾面前坚韧不拔的智慧,而黄耀祥在受到了民间谚语中“树大招风”的启发后,他判断,水稻茎秆越高,其基部因风力袭击而受到折力就越大,因此抗倒性就差。
于是,他设想出新的育种方向—粗秆的“大个子”不抗风,那短小的“矮个子”是不是就能抗风呢?
带着这个疑问,从50年代中期开始,黄耀祥带领着团队四处搜寻具有矮稻基因的品种,终于在1955年收到了一株来自广西百色的“矮仔粘”。
相比高秆的“广场13号”,这株“矮仔粘”的苗高不到前者的一半,而黄耀祥早期培育出来的矮稻其综合性状和产量也比不上前者。
如何扬长避短,综合两个水稻品种的优势?黄耀祥先通过以广西农家品种“矮仔占”为材料,选育出“矮仔占4号”,而后将“矮仔占4号”与“广场13号”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与系选,成功培育出了首个通过人工杂交方式获得的矮秆籼稻品种“广场矮”。
“广场矮”约90至100厘米高,不仅具有育成矮秆的特征,还抗倒伏,其结实率也很高,将水稻的亩产从250公斤提升至400至450公斤,标志着水稻产量的一次重大突破。
直到1966年,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才培育出被称为“奇迹稻”的矮稻良种“IR8”。而“广场矮”比“IR8”快了6年,被学术界称誉为“开创了世界水稻育种的新纪元”。
黄耀祥对待水稻育种的研究,有一种孜孜不倦、精益求精的精神。林青山是黄耀祥的学生,他记得,在那个电脑还没普及的年代,黄耀祥写文章报材料都会一字一句地细细斟酌,反复推敲,改的次数多了,纸面都被写满改花了,只得重抄一次。“一份材料反反复复抄许多次,直到满意为止。”
而黄耀祥并未停止对水稻的钻研。
水稻能否实现稳定的高产性能,不仅取决于种子遗传潜力,还与种植稻种的环境有关。黄耀祥所在的广东,不仅在夏季台风暴雨频发,甚至出现洪涝,且早春连绵阴雨,容易造成烂秧,还常年高温多湿。
针对以上环境特征,黄耀祥开展了“特高产、超高产育种”的研究,开创高光效株型与高光效功能相结合的“丛化育种工程”,创建了以矮化育种为代表的生态育种理论。
中国水稻所所长熊振民将“水稻矮化育种”视作“中国育种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,在国际水稻的研究上也是划时代的成就”。1978年,黄耀祥的“水稻矮化育种”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,与墨西哥的小麦矮化育种一起,引领了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。
“竹竿子里面出品种”
广东的夏季热浪滚滚,常叫人只想蜷缩在室内。但黄耀祥坐不住。比起待在舒适阴凉的工作间,他更想去田里看看,亲手触摸那一株株稻穗。
烈日将皮肤“烤”得黝黑,他毫不在乎。黄耀祥常戏称自己是“竹竿子里出品种”,到了田间,用竹竿挑动水稻植株,细细观察,筛选出好的种子。只有双脚踩在泥土上,看到、摸到稻穗才能让他安心。
周边的农民认得他,亲切称其为“祥叔”。科研助手江奕君回忆,工作期间,常有农民来信求种,黄耀祥总是耐心记下后把种子寄出。他坚信育种工作不能凭空想象,必须深入田间地头,倾听农民不同的意见,比较不同品种的差异,按照需求改良。
黄耀祥终日活跃在育种一线。后来,紫外线不仅晒黑了他的皮肤,还让他在晚年患上了“青光眼”。视力一点点减弱,可他的脚步没有停歇。看不清,走不稳,那就带上放大镜,拄着拐杖和竹竿去。
这个习惯似乎未曾断过。1973年,陈顺佳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工作,成为黄耀祥的助手。据其回忆,共事十来年间,60多岁的黄耀祥仍保持对稻田的热情,频繁下田。
到了晚年,老年时,曾有人问他:“‘人到暮年万事休’,还到处奔波干什么?应该好好享享清福了。”但他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。
黄耀祥每年会回家乡开平几次。开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种子站原站长周之光回忆,那时黄老已八十高龄,仍坚持拄拐杖下田,拦都拦不住。“黄老不服老,你不让他下田他还会跟你生气。”
关于育种,黄耀祥似乎总有使不完的气力,时常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。有时田埂不便行走,他便让年轻人背着下田。视力减退,他就把水稻捧起来靠近眼睛观察,再不行就用放大镜看。看完田间水稻后,他又回房间用放大镜看水稻相关的文字资料。
在家人眼中,黄耀祥是名副其实的“工作狂”。妻子刘金羡曾说,旅行途中,只要有人谈及水稻,黄耀祥马上就在工作上。“除了水稻,他的脑子里没想过其他事情,家里堆得到处都是稻种。”
黄耀祥住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内一座二层楼房。房子一楼,有一间20多平米的房间,被命名为“论稻居”,是他晚年工作的地方。
家更成了一个“谷仓”。曾有记者到他家采访,下意识就踮起脚尖、小心翼翼行走,生怕踩到谷穗。当时,屋内遍地谷穗,撒在起居室的地板、茶几、乒乓球台及书柜的抽屉里,也沾在黄耀祥穿的棉布鞋面上。
有记者好奇:这么多的谷穗,会不会招来老鼠?刘金羡打趣道:“我们家的老鼠可有眼光了,专吃口感最好、营养最高的新品种样本,不管藏在哪个柜子里都能找到。”
还有一次,黄耀祥将薪水遗忘在一堆稻谷上。过了好几天,刘金羡先发现了,定睛一看,钱已被老鼠咬破了几个窟窿。那段时间,家里一度成了老鼠的“乐园”,直到保姆送来一只猫才有所好转。
其实黄耀祥不怕老鼠到家“做客”,只怕珍贵的育种材料没地可种。
数十年如一日,黄耀祥对种子的爱惜始终贯穿他的科研生涯。20世纪60年代,黄耀祥的育种工作受阻。他偷偷保留起几十粒“广秋矮”变异株种子,但一直找不到机会栽种。
宝贵的育种材料再不种就等不及了。没种下的珍贵种子像是头上悬着的一把剑,让他寝食难安。人民要吃饭,进行到一半的试验又哪能说停就停?
后来,他把目光盯上家里二楼破旧的小阳台。1967年春天的某个午后,他买来几个大瓦盆,一个个往阳台上搬,开始了“天台育种”。
没有土,他就用书包装满土背回家。没有肥料,他就用灶膛里的土木灰或少量黄豆捣碎,泡在尿盆里发酵成肥料。水稻快成熟时,他又架起铁丝网罩住盆,防止鸟雀伤害种子禾苗。
五十余年的育种生涯中,黄耀祥的眼里只有水稻,没有一刻想要放弃。
他说:“一到稻花飘香的季节,要想到我那些正在试验的新品种,我的心又飞到了那广袤的田野上。”